
引 言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旨在规范各地彩礼乱象。婚俗礼仪积淀了繁杂悠久的历史因素,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彩礼这一习俗。彩礼一方面代表男方或男方一家对待娶妻的诚意、对于订立婚姻的尊重,但另一方面正因“彩礼”的财产属性,这一礼数逐渐失去其本来意义,一段婚姻最终能否结下良缘,成也“彩礼”,败也“彩礼”。索要、炫耀高价彩礼,媒婆、婚介等怂恿抬高彩礼金额,彩礼金额普遍过高等问题层出不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本文笔者通过梳理近年来我国涉彩礼相关法律法规的变迁、司法实践观点,对《规定》中的法条作一一解读,以期在《规定》正式生效之际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解读一:《规定》的出台填补了民法典对彩礼规范的空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了彩礼返还条件,但在实际案件中,存在着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共同生活、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很短,针对上述两种情况,彩礼的返还无法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同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亦未就彩礼范围、给付彩礼数额价值、返还考量因素等进行明确规定。
202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通过了《规定》,该规定进一步填补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针对彩礼规范的空白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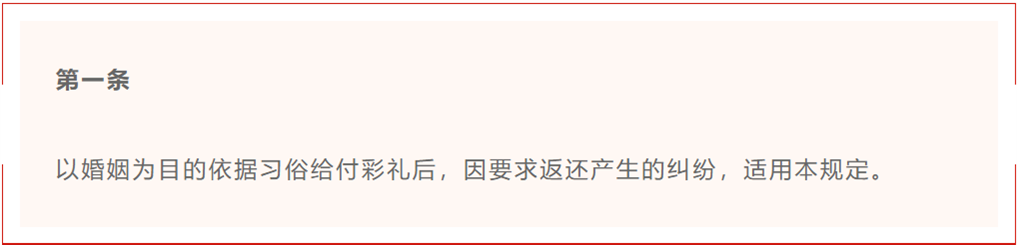
解读一:《规定》适用范围。
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须系基于风俗习惯,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而给付,有给付彩礼习俗的,是认定彩礼的前提。因给付彩礼而产生纠纷,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适用本司法解释的规定。
解读二:关于彩礼的认定。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由于“习俗”的内涵并不确定且因各地风俗给付的金额和种类、名称不尽相同,故人民法院在习俗的认定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在(2023)鲁0921民初925号案件中,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按照农村风俗向被告支付的换手绢钱10100元、订婚当天支付的80000元,结合当地风俗及收入水平,本院认为均属于彩礼的范畴,被告主张80000元系保证金以及押回2000元,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在(2023)辽04民终387号案件中,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上诉人没有否认接受了被上诉人家给付的彩礼钱,至于上诉人所称7万元彩礼是分2个袋子给付,并不影响7万元是彩礼的性质。按照本地的婚俗民情,男女双方在结婚前,由男方父母付给女方一定数额金钱作为彩礼是民间婚俗的常态,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否认7万元是彩礼钱而强调是保胎钱没有充分证据,法院对其此诉请不予支持。
根据以上案例,若双方均采用特定的名称指代款项、赠予之物且讨论的语境系在谈婚论嫁的背景之下,符合普遍认知,则宜认定具备彩礼的属性。当事人若就财物的认定不属于当地习俗,不宜认定为彩礼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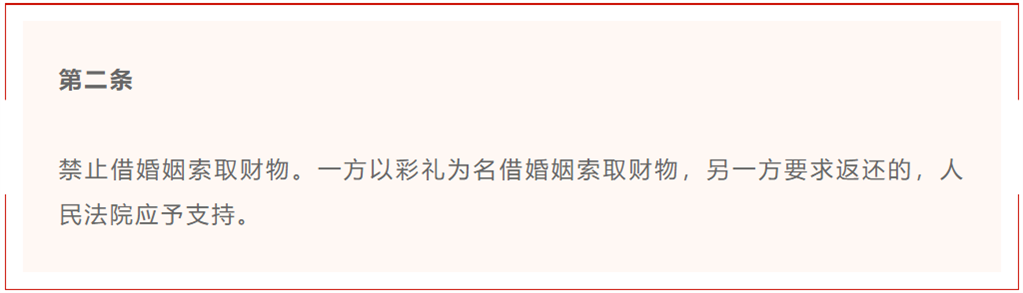
解读一:进一步明确“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返还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姻当事人的一方(父母或其他亲属)以结婚条件为由,要求另一方交付一定数量金钱或其他财物的,此时作为结婚交换条件的财物虽名为“彩礼”,实质上已侵害了婚姻情感自由与财产权利,系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一方根据《规定》第二条,请求对方返还,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综合考量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时间、双方过错等因素酌定返还数额。
解读二:司法实践中对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认定。
在《规定》意见征求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收受彩礼后携款潜逃或者短期内多次以缔结婚姻为名收取高额彩礼后无正当理由悔婚的,应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但除收受彩礼一方自认外,实践中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相对方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以及“收取彩礼后并无结婚意愿的主观因素”,结合既往案例,司法实践中对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分析如下。
将高额彩礼作为结婚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以爱情为基础,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在(2021)赣民申256号案件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是指当事人双方自愿结婚但以索取一定财物作为结婚的前提条件的行为。刘某与钟某定亲,钟某1、江某、钟某接受刘某家支付的292200元彩礼,数额巨大。刘某与钟某只是同居,并未结婚,之后双方发生纠纷,钟某1、江某、钟某接受刘某家彩礼并在刘某与钟某解除同居后不予返还彩礼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收受彩礼后同意结婚,又以索取其他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在(2021)湘0523民初532号案件中,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以身体原因不同意立即结婚,本属人之常情,但后又以要求原告支付4万元置办酒席,是一种对婚约另外增加结婚条件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不符合我国一直正在提倡的移风易俗、婚事简办的价值取向,该行为可以评价为悔约,但只是接近于毁约,并不构成毁约,同时引起原告对未来婚姻的失望,并导致原告起诉,故被告的行为在本案的“附解除条件”的成就中负有一定作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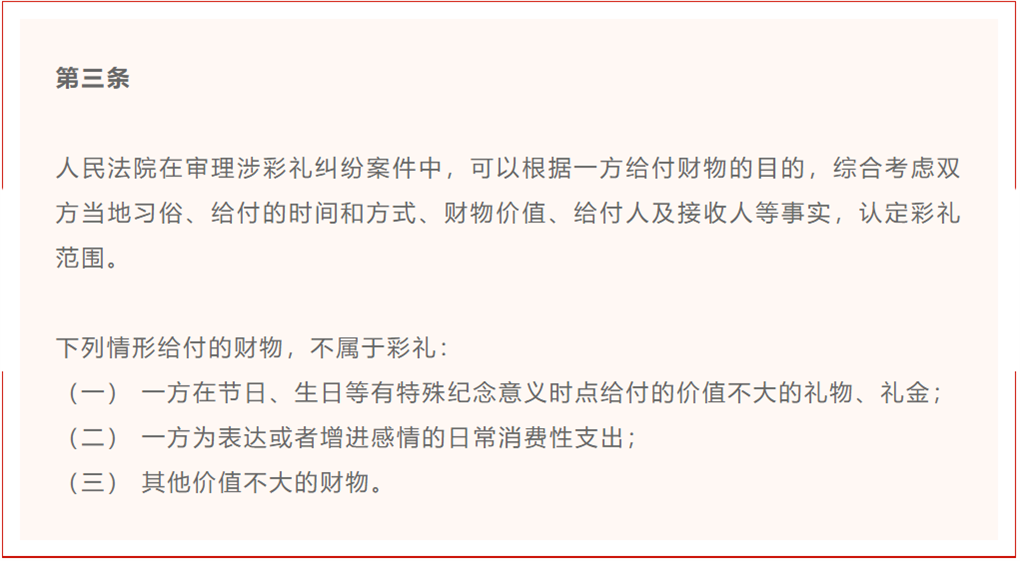
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
(一) 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
(二) 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
(三) 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解读一:厘清彩礼范围,将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进行区分。
情侣双方在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感情相互或单方赠与财产的情况普遍存在,包含了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的意思表示,小额的金钱给付行为属于一般性赠与,在恋爱关系终止时,赠与方不能主张返还。
当事人以结婚为目的赠与一定财物的(如较大额金钱),可视为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当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时,赠与一方可要求予以返还,针对此类情况,法院针对彩礼范围的认定需根据财物的目的,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与一般赠与进行区分。
解读二:通过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
对于合理范围内价值不大的财物(权衡是否属于价值不大的财物,应当综合考量各方经济水平、赠予的方式、数额、用途),各方不以结婚为前提,出于表达或增进感情的礼物及日常消费性支出一般认定为一般赠与。比如在生日、情人节等特定纪念日赠与的礼品,双方在恋爱期间涉特殊含义数字如“520”的转账金额等,该部分赠与一旦将财物交付,赠与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在恋爱关系终止后,赠与人不能主张受赠人返还。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介绍,此类财物或支出,金额较小,主要是为了增进感情的需要,在婚约解除或离婚时,可以不予返还。但是,如果是大额赠与,虽然不属于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范围,也应当考虑赠与的特定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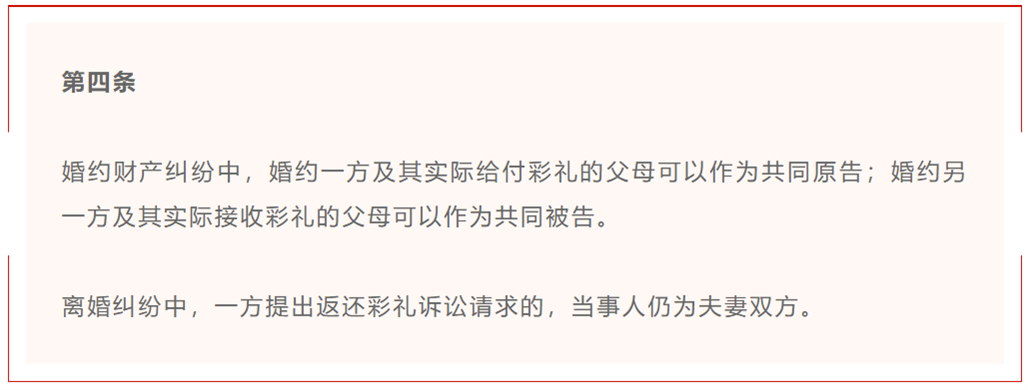
解读一:彩礼纠纷程序问题要充分尊重民间习俗。
在彩礼返还纠纷中,诉讼当事人的确定往往成为争议焦点。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公布的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的案例四中,在审理该案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上,审理法院认为,因案涉定亲礼系赵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三人作为共同被告能够更好查明案件事实并确定法律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缔结婚约过程中,通常是男女双方及其家人、媒人等见证下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完成彩礼的给付。
解读二:《规定》进一步明确彩礼纠纷诉讼当事人的范围。
因此,在确认彩礼纠纷诉讼当事人时,要充分考虑民间风俗习惯,《规定》将程序上的争议进一步明确,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婚约财产纠纷。原则上此类纠纷应以男女双方作为诉讼当事人,但考虑到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为尊重习俗,也为更好查明彩礼数额、实际使用情况等重要案件事实,《规定》明确婚约一方及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二是离婚纠纷。由于离婚诉讼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婚姻外的第三人纳入诉讼程序中。《规定》明确,在离婚诉讼中,一方诉请返还彩礼的,仍应以婚姻双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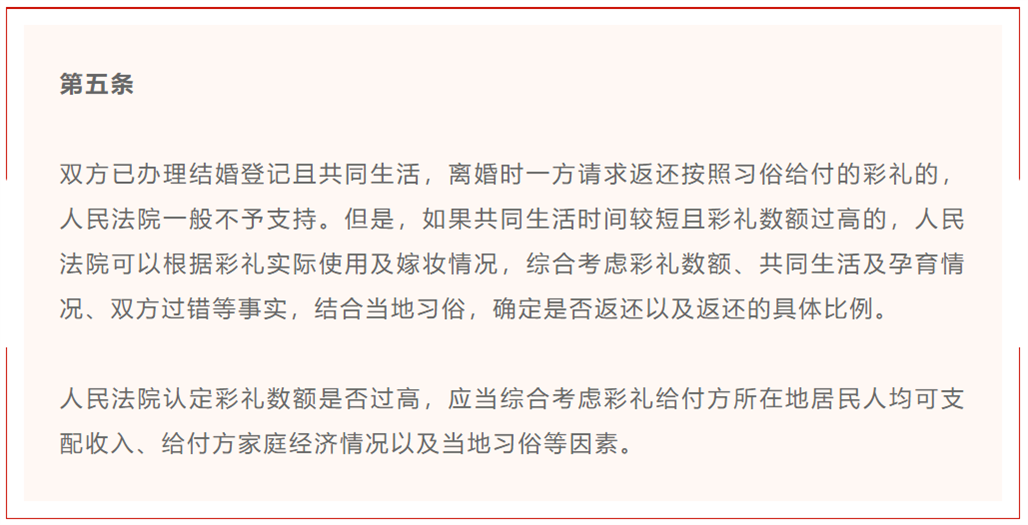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规定》第五条明确了男女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的,原则上不退彩礼,但考虑到实践中存在一方给付高价彩礼后,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多重因素酌定彩礼返还数额及比例。
解读一:共同生活居住的认定。
现实中,夫妻是否共同生活居住是个复杂的问题,而双方共同生活又是一方给付彩礼的重要目的,故如何认定双方是否实际共同生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曾代理过一件诉请返还彩礼的案件,男方与女方婚后常年异地生活,双方就是否共同生活居住分歧较大。
在(2023)桂0703民初277号案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总结归纳了认定夫妻共同生活的几个方面:(1)共同的住所;
(2)夫妻间的性生活;
(3)夫妻共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相互理解和慰籍;
(4)夫妻相互扶助的义务;
(5)夫妻共同承担的其他家庭义务。
此外,双方以夫妻身份共渡难关,如一方生病另一方给予生活照顾、经济支持等也可以视为是履行夫妻照顾义务及家庭责任。因此,在判断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时,既要考察主观上是否有共同生活的意愿,也要考察客观上是否共同履行夫妻义务和家庭义务。
解读二: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时彩礼返还考量因素。
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完成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定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居住。如今“闪婚闪离”现象频繁发生,而给付彩礼一方有的是举全家之力,导致部分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现象仍然存在,为进一步扫除以结婚为名索要“高价彩礼”的陈规陋习,平衡婚约双方家庭的利益,本《规定》充分考量彩礼数额及使用情况、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有无子女、双方过错等因素,酌定彩礼是否返回及返回比例问题。
(2023)新40民终682号案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马某与帕某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后双方生活时间仅有两个多月,并未真正形成互相扶持照料、互相履行义务的家庭共同体,未实现婚后共同生活的目的。鉴于14万彩礼部分用于帕某购置家电、家具、帕某个人生活用品及金饰等嫁妆,部分用于筹备婚礼,一审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及诚信原则,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时间、马某家庭情况等因素,酌定判决其返还5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判决结果。
解读三:“高价”彩礼的认定问题。
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变成一种物质交换,不仅给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然而,对于何为“高价”彩礼,受限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法律规定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划分,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地经济水平、普通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从司法个案中予以探究。
在(2023)甘05民终586号案件中,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某1与林某1订立婚约,实际给付现金彩礼139400元及“三金”(钻戒1枚、金手镯1个、金项链1条),已明显超出当地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经济范围,属于高价彩礼。在(2023)赣10民终109号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案涉彩礼数额达到189600元,已超过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属高价彩礼。
《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明确,在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上,要充分考虑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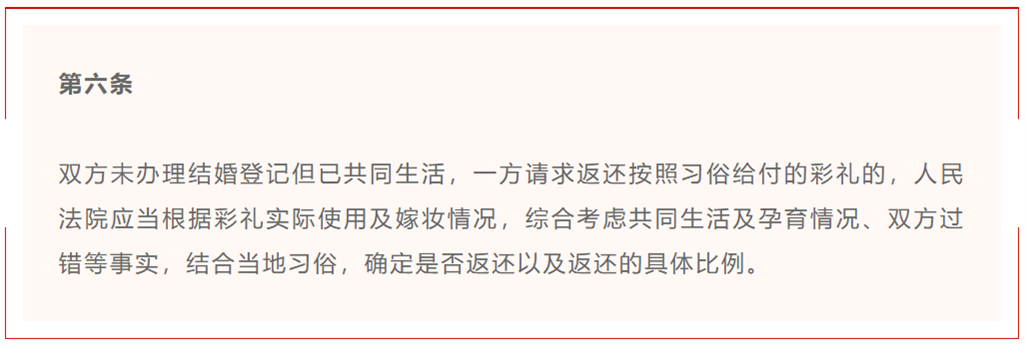
解读一:为平衡不同合法权益,彩礼纠纷要注重考察“夫妻之实”。
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男女双方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因共同生活居住形成的“夫妻之实”。共同生活居住既是给付彩礼的重要目的,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类似情况。此时,如仅仅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为由判决接收彩礼的一方全额返还,将有违公平原则,亦不符合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宗旨。
解读二: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返还彩礼时考量的因素。
《规定》第六条就是考虑到上述情况而产生,为了平衡不同的合法权益,在该情形下,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至于失衡。
在最高院发布的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二中,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自2019年2月开始共同生活,并按习俗举行了婚礼,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满2周岁,原告诉请要求返还彩礼,对被告赵某明显不公平,法院不予支持。在(2023)赣0731民初4731号案中,原被告系男女双方的父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之子与被告之女在一起共同生活2年左右,现已分居且双方无登记结婚的意愿,缔结婚姻的目的现已不能实现,被告收取的彩礼236000元,数额较大,但考虑到双方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且生育了1名子女,最终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30000元。在(2016)苏10民终2551号案中,经查,男方共向女方给付168000元现金彩礼及总金额41294元的五金,审理法院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共同生活一年半之久,部分彩礼已经用于筹备婚礼和日常生活,女方陪嫁物品归男方所有,且期间女方曾经怀孕流产,最终酌定女方向男方返还30000元。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共同生活居住是夫妻关系的核心,故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财产情况、彩礼使用情况、孕育子女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确定返还数额及比例。
结 语
《规定》的出台实施有助于引导社会群众树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婚姻理念,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婚嫁负担。对于《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仍然需要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也期待各地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积极探讨本《规定》的适用问题。